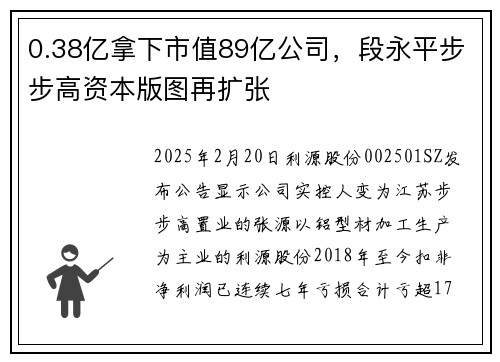
17岁就参与日本侵华战争的他临终忏悔: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安门广场,任人踩踏
- 8

“我对不起被我杀害的中国女人和男人们,以及他们的家人,我罪该万死。几十年前在中国境内,我干了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,我不能回避,也不能粉饰,因为那是战争,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。我自知罪恶深重,所以希望我死后,能有人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去,撒在天安门广场,让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我,就算是我的赎罪方式吧。”
这段话摘自侵华日军大岛中典写给“遗言收集者”袁苡程的信件。

《见字如面》剧照
第三季《见字如面》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观众跟随朗读者、演员董勇走完大岛的一生,从战前到战后,从疯狂杀戮到内心煎熬。面对这样的公开忏悔,沉重之余,值得反思。
大岛中典:战争召唤内心的恶魔,杀人成为最刺激的人间游戏
1937年,年仅17岁的大岛中典作为增补入伍的新兵,加入侵华战争。离开家乡时的他几乎没有任何不舍之情,因为在他看来,天皇号召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融进了他沸腾的年轻血液。大岛所在部队在多日的狂轰滥炸后,首先攻陷了中国南方的古城苏州。
无尽的杀戮由此开始。28个中国人,倒在他的脚下。200多名妇女,任人奸淫。
“多数人都知道吸食毒品会上瘾,而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会知道,杀人也会上瘾,那才是最残忍的瘾,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和控制别人生命的生杀大权的自豪感,也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。当杀戮不但被允许且成为必须做的事时,你就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。我们都成了杀人狂。”
1945年8月15日,日本无条件投降。战后,大岛中典作为幸存者回国,成为一名牙医。本以为生活会趋于平静,但作恶的梦魇始终缠绕着他,妻子、孩子、女婿、孙辈却继续失踪、夭折甚或意外死亡。哪怕他跑到美国,试图隐瞒历史,都无法摆脱噩梦的困扰。
一个起初连杀鸡都不敢的男孩,到杀人如麻的刽子手。被异化的大岛中典,既是战争的共谋,更是二战的牺牲品。曾经的“快感”成为他梦魇的根源,无法填补,更难以逃避。即使他皈依佛门、“放下屠刀”,“立地成佛”也是虚妄。唯有直面反思,才能从中感到一丝内心的平静。
许子东:如果日本人能普遍具有忏悔意识,中日关系会好很多
大岛中典在信中呈现出人性的种种面向,加入侵华战争的他,通过战争对人性“恶”的无限扩大,从虫子都不敢虐待的人走向杀人上瘾的两极。在国家的利益之前,他的个人行为自然归属为集体行为的折射,在统一战线的侵略里,沦为了一匹泯灭“善”的恶狼。
于是当战争的浪潮退去之时,大岛中典必须要去面对他人生里永远无法应对的一场错位。值得一提的是,大岛中典的创伤并非单纯的战后心里综合症。家人接连的失踪与死亡所产生的宿命性,是一种无形的审判,更是将他的梦魇推向了极致。
《见字如面》剧照
jbo竞博·电竞app正是这种不断缠绕又加深的折磨和痛苦,让他对自己在战争里的罪行,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,做出了忏悔。这种忏悔,不是基于集体,而是始于个人。
虽然这些无法抵偿他所犯下罪行的万分之一,但对于这份不加回避与粉饰的忏悔,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他的意义。正如许子东所言:“如果日本人能普遍具有忏悔意识,中日关系会好很多。”
史航:反思战争?反思战败?
面对大岛中典的沉重忏悔,嘉宾史航从个体出发,质问集体:战后的日本,究竟是在反思战争,还是反思战败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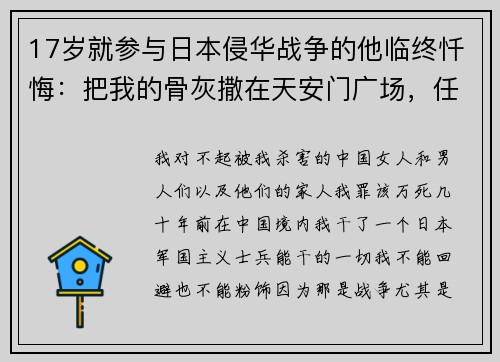
与大岛的诚恳与痛苦不同,作为战败国的日本,仿佛在战后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,反思的并非是战争本身,而是战败的事实。
如果说个体不具有代表性,那么作为轴心国主力的德国与日本,两个国家,在当今社会人们眼中却是完全不同的形象。
德国柏林犹太纪念碑群,是为了祭奠那些在二战里受害无数的犹太人,而日本的靖国神社里仍供奉着二战里死去的甲级战犯。
德国铲除了纳粹主义的基础,而日本的头号战犯裕仁天皇并未得到清算,连他的儿子仍然是一位天皇。包括甲级战犯嫌疑人也被无罪释放,依然能成首相。
反省罪行的德国与掩盖历史的日本形成对比,日本反思战败的事实暴露无遗。
《见字如面》剧照
大岛中典一生的悲剧性,源自战争。他的忏悔,尽管姗姗来迟,但依旧意义深远:作为集体的构成者,他的反思面对中国,指涉日本。也许他无法代替自己曾经的祖国,但忏悔信存在告诉世人:正视历史,需要勇气,更需要一颗真诚的心。
